东北的冬日是实实在在的寒的,后视镜中看着因为疼痛而略显佝偻的身躯蜷缩在丫头的怀里的他,听他呢喃着有关母亲,有关妹妹、有关我的曾经。我知道,这一切你都记得的、记得母亲记得的我们的所有的那些;记得她会时常轻柔的打开那些属于年少时儿女们的过往,仔细的看,认真的想,深刻的念,然后幽幽的流泪。我知道的,我真的全都知道的,你常常诉说的有关母亲的那些记得何尝不是你的记得?你何尝不记得我们的这些?你何尝不是更是记得母亲也是记得的这些?母亲珍藏着的我们的曾经,而今,你便珍藏着母亲的珍藏,你是把我们和母亲一起放在你已经有些单薄的身躯里,深深的埋藏的。你知道的,母亲是极疼爱我们的,你知道她不在了,我们会想,我们会觉得孤单,可是,你更想,你更疼。于是,你就这样把这三个人一并装进你的灵魂,日夜在生命里守护着,守护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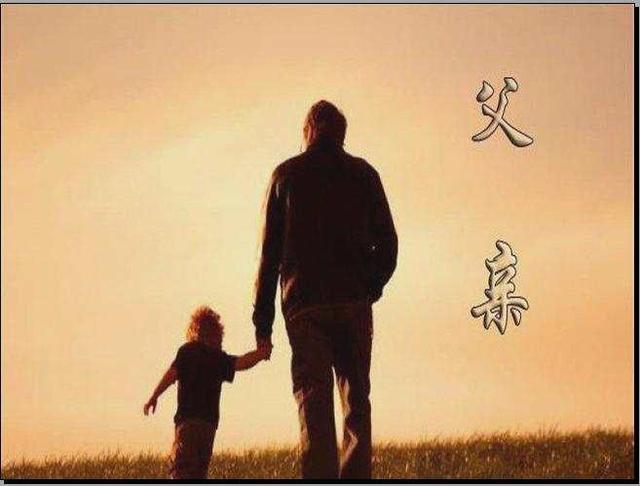
这一刻车厢中的气息在弥漫,汽笛鸣响的声音凝固在耳际,刺疼了鼓膜,鼻尖的酸楚穿透了心底最后一道防线,转身,泪,奔腾而下。我还能再看你多久?你的身影是不是要渐行渐远,继而消失在云水间,只剩下那一圈圈晕开的波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车在公路上疾驰。想起夕阳中的稻黄,是一场意外,迎着汩汩的速度,直直地撞进视线。眼角微微的疼,记忆像被风含过的一湖水,平仄起伏 ……

炊烟,稻黄,镰刀,暗黑的泥土,以及躬着背的父亲,如一帧帧精美的片段,次第汹涌。那些念想迈着几不可闻的脚步,绕过握着方向盘的手。远处的村庄吐着一缕一缕的炊烟,温柔蓬松如父亲的鼻腔里冒出的烟圈时,我所有的挣扎,溃不成军。一场稻黄,击中内心的柔软,潜藏的乡愁,排山倒海。加速,再加速。风驰电掣的速度会不会再一次地穿过一片又一片汹涌的稻黄,纷纷扬扬,像一场来不及诠释的思念,盛大,缠绵,生动,澎湃。远山,眉峰聚,远水,眼如波。而我,竟被陡然漫出的委屈,一点,一点,泅伏。好比,再次归家的游子,揣着热切的遇见,却只能碰到一扇冰冷的门。时光里的母亲,模糊且遥远。童年,庄稼,小河,流水,以及一些其他的印象,如一棵埋在地底的藤,呼啦一下拔啦起来,看到记忆成了一部回放的电影,快速地倒带。旧的片段,柔韧如绳,深深浅浅地,抽过。一声狗叫,划过乡村的寂静。老房的灯火,袭击着发呆的沉陷。橘黄的灯,漫溢着温柔的芒,揉过我的眼。一些温情,止不住地,泛滥。那时,母亲在灶台前忙碌,她正掀开锅盖,浓浓的鸡汤香味长了脚似的,一股脑儿地奔向推门而进的我,又长了一双手似的捏着我的鼻子不由分说地灌下去。却险些被满屋扑鼻的浓香绊了个趔趄。而母亲,被白白的汤雾笼罩,侧着身子,拿着勺子,捏着锅盖,全神贯注的倾斜,像一弯饱含深意的弧度……

父亲呢?晕黄的灯光下,小小的灯泡,无力且迷茫,父亲坐在炕沿儿上,认真地捏着饺子。小小的,圆圆的,密密麻麻,一溜儿排过去。竹篾上站立着均匀且神气的饺子,父亲的头颅低低下垂,如此专注,是在完成世上最伟大的作品了。灶膛前添着柴火,火光一闪一闪,扑上母亲的脸颊,深刻的皱纹,在温暖的灶火前毫不留情地披露。父亲站在灶台前,将那些饺子“噗噗”地跃入锅中。雾气袅袅,模糊了父亲的眼,却依然费力地望着水里沉浮不定的饺子,弯腰凝视的模样,是一把镰刀,割断岁月的葱茏。这些,每一件事都是需要时间,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像姑娘的绣花,像裁缝的制衣,用心和情酿出最甜最香的蜜,让人一辈子的念想。头顶上橘黄的灯光,温暖,柔软,平和。小小的屋子里,父子和母亲为我准备的东西,如小山一样。此刻,它们一样一样地搬空,一样一样地装到车子的后备箱。老屋,瞬间松垮下来,空荡荡的,显得更旧,更沧桑了。似乎他们恨不得把这老屋,把自己也打包装好,一起随我的车子去才觉得安心……

命运之石从身后而来,我不知道它来的方向,我无力躲避。亲情!精诚未必金石开。感觉!输怨难再从头来。真就只能是一个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守我之念,能不能如心所愿?我望我城,可否守你于城?对望,凝聚成一生的念念不忘。江山此夜,我只愿护你片刻安好。人生如果没有如果,就没了梦见,即便哭了,醒来,却只能笑着。因为曾经有你,只是,烟火过后的心碎,化蝶伴泪飞。待到,那一日,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转世,再成为值得你爱,深得我爱的人。就让缘,空,悟,善,来修得下一世情缘吧,只求,遇见你的那世,不要再让你受太多的苦……
在这世间,万千人中,只是当遇见了某些人,某些事,才不得不选择沉默面对。只有这样,心才不再痛,不去想,不再伤,不久念,只求简单幸福。
冬!捧一把白雪,净美之间不语,不冷。心中若有爱,温暖如花开,自可于寒冷中,寂寞绽放!尼古丁的作怪,叶绿素的迷香,打开文字匣,粒粒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