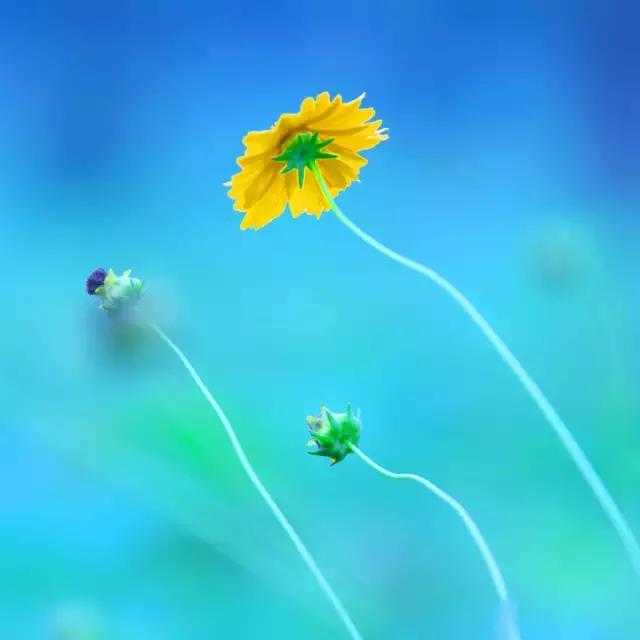父亲86岁了,卧病在床。他的心脏,那台供血机器,同样老得无法胜任某些活儿了。它仍滋润着他的大脑,使其散发智慧的光芒。但它甚至已无法使他的腿撑着身体在屋里走动了。不管我怎么比方,他却说这种肌肉衰退并非缘于他的心脏病,而是因为缺钾。他垫着一个枕坐着,背靠着3个枕头,给我提了他的最后要求。
“我还想要你再写一个小故事,”他说,“就是莫泊桑、契诃夫写的那种,你过去常写的那种。就是一些小人物,然后写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我说:“行,为什么不呢?完全可以。”我想讨好他,尽管我已不记得曾写过那样的故事。我愿意去讲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他指的是这类开头:“有一个女人……”之后是情节,也就是两点之间的绝对线,这是我所一直鄙视的。这并非文学方面的缘故,而是因为那样做使所有的希望都不复存在。每一个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创作出来的,他们的命运都应该是开放的。
最后,我想起了一个前些年发生在街对面的故事。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大声读起来。“爸爸,”我说,“这个怎么样?你指的是这样的故事吗?”
从前,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他们在曼哈顿的一栋小公寓里愉快地生活着。那男孩约15岁的时候成了吸毒者,这在我们附近并不罕见。为了与儿子继续保持亲密关系,母亲也成了吸毒者。她说这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她觉得很自在。不久,由于某些原因,男孩彻底戒了毒,并离开了这座令他深感厌恶的城市和他的母亲。母亲在无助和孤独中哭泣着。我们常去看望她。
“好了,爸爸,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说,“一个未加修饰的悲惨故事。”
“但那不是我指的那种故事,”父亲说,“你故意误解我的意思。你明知道还有很多可写的。你把什么都漏掉了。屠格涅夫是不会那样做的,契诃夫也不会那样做。事实上,还有些你从没听说过的,你一无所知的,同样很优秀的其他俄国作家,他们也都写普通的小故事,但他们不会漏掉被你漏掉的东西。”
“爸爸,现在我到底漏了什么呢?在这个故事里?”
“她的长相,比如说。”
“哦,很漂亮,我想,是的。”
“她的头发呢?”
“黑色的,扎着个大辫子,就像个小女孩或外国人。”
“她父母怎么样,家族呢?这使她成为这样的人。这很有趣,你知道的。”
“从城外来的,职业人士。是他们那个县第一对离婚的夫妇。怎么样?够了吗?”我问道。
“对你来说,这些都是笑话,”他说,“孩子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没提到他?他是什么人?或者,这男孩是个私生子吗?”
“是的,我说,他是个私生子。”
“老天,你故事里的人物怎么都不结婚?他们上床前怎么就没时间先到市政厅跑一趟呢?”
“是的,我说,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但在我的故事里是这样的。”
“你怎么这样回答我?”
“噢,爸爸,这不过是一个聪明女人的故事,她来到纽约,充满情趣、爱心、忠诚和激情,而且很时尚。她和她的儿子,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结没结婚,这并不重要。”
“这很重要,”他说。
“行了,”我说。
“行了,行了,你自己知道,”他说,“听着,我相信你说的她长得很漂亮,但我并不认为她有多聪明。”
“是真的,”我说,“事实上,故事的问题就在于此。刚开始那些人物是很不错,让你觉得他们不同一般,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罢了。有时情况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故事中的人物单纯无邪,但她比你聪明,令你甚至想不出一个足够完美的结局来。”
“那你会怎么处理呢?”他问道。他当了几十年的医生,又作了几十年的艺术家,仍然对细节、技巧和手法很感兴趣。
“好了,那你只能先把这个故事搁在一边,直到你和那个固执的主人公之间能达成某种一致。”
“你不是在说傻话吧?”他问道。“再来一次,”他说,“刚好今天晚上我不打算出去,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看你这次能说些什么。”
“好吧,”我说,“但这可不是几分钟的活儿。”下面是我的第二次尝试:
从前,在我们街对面吗,住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是我们的邻居。她有一个儿子,她非常爱他,因为从他一生下来她就了解他(在他无助的胖乎乎的婴儿期,在他7到10岁前后打打闹闹的时期)。这个男孩刚进入青春期就染上了毒瘾。他并非不可救药,事实相反,他是个很有希望的人,一个理论家,一个成功的煽动家。他反应敏捷,极具天赋,为校报撰写煽动性的文章。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他通过重要的关系,不停地向“低曼哈顿”报刊亭发行一种名叫《啊!金马!》的期刊。
为了不让他感到内疚(她说,因为内疚感是当今美国百分之九十铁石心肠的人的临床诊断症状),而且也因为她始终相信应该在家改掉坏毛病以便仔细观察,她自己也成了一个吸毒者。她的厨房闻名一时——成为了那些自以为清醒的知识分子瘾君子聚集的中心。其中有些人感觉自己像柯尔律治一样有艺术气质,还有些人自认为像利尔一样具有科学和革命精神。尽管她自己经常感觉飘飘欲仙,但作为一个好母亲的良知仍未泯灭,她准备了许多桔子汁、蜂蜜、牛奶和维他命片。然而,除了最多一星期作一次肉辣酱以外,她什么菜也不做。我们和她聊天时,作为邻居,她不无忧虑地、严肃地解释道:这是她融入年轻人文化的一种表现,她更愿意与年轻人而不是她的同龄人在一起,那是她的荣幸。
有一个星期,当那个男孩打着瞌睡看着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时,被坐在他旁边的厉害而从此使他改变的女孩子用肘狠狠地击了几下。那女孩马上又给他吃了合他口味的杏仁和坚果,严厉地对他说话,然后把他带回家。
她听说过他和他的作品,她自己编辑、出版了一本叫《人类仅靠面包生存》的极具竞争力的杂志,并担任撰稿的工作。随着她那散发着热量的肌体的频频出现,他无法抵挡地再次对自己的肌肉、血管及神经系统感到兴趣来了。事实上,他开始爱它们,珍惜它们,并在《人类仅靠》上发表有趣的小诗赞扬它们:
我的手指超越了
我那先验的灵魂
肩膀放松了
牙齿使我完整
为了头上的那张嘴(那个闪烁着意志和决心的光华的完美之物),他买来了硬苹果、坚果、麦芽和大豆油。他对他的老朋友说,从今以后,我想我会保持警觉。我要去旅行。他说他要去做一次心灵的深呼吸。妈妈,你呢?他好心地问道。
他的谈话是那样的光芒四射、精彩纷呈,以至于他同龄的邻居的孩子们都开始说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染上过毒瘾,只是作为一个记者去作了一次体验采访。这位母亲曾尝试了好几次想要改掉,因为没有儿子和他的朋友们陪伴而染上的孤独的毛病。她努力地达到了使人能够容忍的程度。儿子和他的女孩还是带着他们的电子油印机搬到另一个区的树林边去住了。他们非常严格,说除非她能60天不沾毒品,否则他们不会再来看她。
夜晚,母亲孤独地在家里哭泣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7期《啊!金马!》。似乎只有它们才对她依然忠诚。我们经常过街去看她,安慰她。但只要任何人提到自己的某个孩子,或在上大学、或在医院、或退学在家,她都会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然后,痛哭流涕,面目全非,哭啊,哭啊。故事结束。
父亲先是一阵沉默,然后说:“第一,你很有幽默感。第二,我看你讲不出什么平常的故事来。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然后,他伤心地说,“第三,我想,那意味着她从此孤独,他的母亲就这样被抛下。孤零零的,也许生病了?”
我说:“是的。”
“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孩子,出生在愚蠢的年代,生活在傻子之中。结局,那个结局。你可真行,写出了这样的结局。”
我并不想争论,但我不得不说,“好了,这不一定就是故事的结局,爸爸。”
“就是的,”他说,“一个人的结局竟是这样的悲剧!”
“不,爸爸,”我哀求着说,“不一定是这样的。她才40岁。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可能有100种不同的选择。成为一名教师或社会工作者。让吸毒成为过去!有时这比获得硕士学位更可喜。”
“笑话!”他说,“作为一个作家,这就是你的主要问题所在。你不愿意承认它。悲剧!明显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没有希望。这就是结局。”
“哦,爸爸,”我说,“她能改变的。”
“你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你必须直面生活。”他喝了几口硝酸甘油。“拨到5,”他指着氧气瓶上的刻度表说道。他把吸气管塞进鼻孔里,使劲地吸着气,闭上眼睛说,“不。”
我答应过家人,每次争论时都让他能强辩到底,但这次我的责任不同。那个女人,住在对街,她是我杜撰的人物。我为她感到遗憾。我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那房子里哭泣(事实上生活也不会像我一样没有同情心)。
所以,她确实改变了。当然,她儿子再也没回过家。不久,她成了东村社区诊疗所的一名接待员。大部分顾客是年轻人,有些是她的老朋友。那儿的主治医师对她说:“如果我们这个诊所能有3个有你这样经历的人……”
“医生是那样说的吗?”父亲把氧气管从鼻孔里扯出来说道,“笑话。又是笑话。”
“不,爸爸,真的可能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世界。”
“不会的,”他说,“首先,真实的情况是,她会回到从前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她却没有。”
“不,爸爸,”我说,“是那样的。她有了一份工作。忘了吗,她在那个诊所工作。”
“她能干多久?”他问道。“悲剧!你也一样。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正视人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