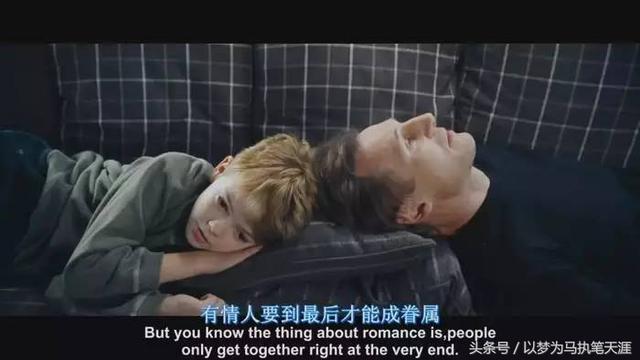题记:雏莺文学社是我在高中时经营的文学天堂。为它,我哭过、笑过、徘徊过、犹豫过,但最终我和我的同伴们咬紧牙关将其坚持了下来。也许在许多人的眼中它根本不值得一提,认为它是那样的渺小或者荒唐,可是不管怎样,我都愿意将属于我和它的故事永远地珍藏在心扉,因为它毕竟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段印记……
今夜无眠,小屋的门正被风轻轻地推开着,写字桌上的烟灰缸也被一根根燃尽的香烟头添饱了肚皮。胸前的《雏莺》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之时,我才知道我哭了。
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高中时我的活动圈子有一些和我一样爱好文学的同学,我们都想妙笔生花,让缪斯女神朝自己微笑。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我是较早便开始主动投稿和发表作品的一个,常常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和编辑部的来信,在这之中要数各校园文学社团和民间小报居多。对那些校园文学界的活跃分子,我很羡慕他们,小小年纪便发表了好多作品不说,还一个个地办起了校园文学社团编辑校园文学报纸。接触这方面信息多了以后,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便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为何不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社呢?当这个提议告诉我那些“臭味相投”的老兄门时,很快便得到了一致通过,大家不谋而合。
说干就干。记得是在一个星期天的夜晚,我们在教室围着一张课桌,借着蜡烛微弱却孕育着无限希望的光亮,你一言,我一语,确定了文学社,社报的名称,组建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商议了社员的吸收原则和第一期刊物的资金筹措办法。烛光映照着我们几个意气风发的脸,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现着无比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终文学社初具雏形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欢呼雀跃,有的竟跳了起来。
当夜作为社长的我,在宿舍架子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平日宿舍里卧谈会最为活跃的我一下子一言不发,让同舍的几个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竟误以为有了心中的她,搁平时,我早给他们分辩了起来,可此时,我只笑了笑,没有说话。
生性善良的我,从小好像就对文字颇感兴趣,而数字则和我是一对冤家。语文成绩常常是高于自己的数学成绩,在班里也独占鳌头。特别是作文,生活在农村的我并没有良好的文学熏陶,没有什么课外读物,甚至爸也没有给我买过一本文学读物,不识字的妈则是更不可能给我买了,因为妈不识字。但恰恰相反的是,我的作文则是班里写得最好的,经常是被当作范文在班上读的。因而打小便想当个作家,想发表作品,想让自己的名字随着文章一起上报。至于自己办文学社、编刊物则是那会儿压根没有想到过的,现在有了自己的文学天地,我又怎能不高兴和兴奋呢?想着“雏莺”经过自己的努力,将来的如何如何,我豪情满怀。那刻甚至想到了将来“雏莺”走向全国获奖时,自己登上领奖台的那一刻,肯定是热泪盈眶的。其实两年以后,自己真的在北京登上领奖台时,却异常的平静。那个对于我和“雏莺”的极不平常的夜晚,便如此的过去了。
二
和时任雏莺文学社主编的李彦辉同学怀揣着整理好的稿件,拿着七凑八拼来的一百多块钱走进街上东门桥附近的润芳打字部时,我感觉自己好骄傲、好伟大。再过不了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到由自己主编的刊物了。我这样兴冲冲地想着。
结果那天我们在打字部呆了整整一天,我们几乎是守在打字员的身旁看着稿件上的字一个个地被敲打了出来,当打完所有的稿件后,时针已指向下午六点了,按原来的计划,再过半个多小时,便可油印完毕装订成册了,可不凑巧的是电脑出现故障了,打进去的东西全部暂时消失了。我们一下子如遭霜打了的秧苗,半天抬不起头。好不容易等电脑恢复正常,时针已指向六点四十了,我们再也无法等了,因为七点钟就要上晚自习了,最后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等下晚自习以后再取。这时,一整天没有吃饭的我们才觉得肚子饿了,匆匆赶到街上一家叫三八饭店的地方,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吃了一大碗煮方便面。还挺乐观地认为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国梁今后定能成大器也。
直到30多本油印小册《雏莺》捧到我们怀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踏实了,将这些油印小册分发给全校各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都知道145班办起了一个文学社,并有自己的刊物,一下子大家对这个新事物的关注之情便全部流露了出来,询问的,投稿的,想入社的,看到这种大好形势我们几个都很高兴地忙碌着。而我却捧着第一期刊物在发愁和犯难,第一期出来了,第二期又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我们几个一直垫支吧,这不是办法呀。这时我想到了学校,想到了学校校长梁建发老师,想着他们应该支持的,心里却还是七上八下的,万一他们不支持怎么办呢?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学校校长梁建发老师是很开明的那种,不仅对我们进行了表扬,而且很是热情地帮我们出谋划策,想法从县教育局和学校内部给我们文学社拨了1500块钱的活动经费,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在以后“雏莺”的成长道路上,梁校长一直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使“雏莺”由原来的16开油印小册,发展到以后的四开四版的胶印小报,确保了我们文学社和社报后来在全国同类校园文学社团的领先地位。而假如没有学校和梁校长的大力支持,甭说发展壮大到最后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是存在下去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提起梁建发老师,我想多说几句。在学校办文学社和毕业之后的这段时间里,有幸和他交往、走进和了解他。我上高一那年,他从二中调到我们学校,人很正直、干脆,办事有魄力。特别是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那段日子,他更是一直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我都将永远铭记于心中,将来如能有所作为的话,便是我对梁老师最好的报答。这时我想起这样一件事,还是在学校办文学社那会儿,我跟江苏一位在全国校园文学界挺有名气的老师打电话,他说:“一般情况下理科出身的校长,对文学社总是压制的。”这时我对他说:“老师,我们校长便是个例外,他虽然是理科出身,但他对文学社的支持是不亚于任何一个文科出身的校长的。”说这话时,我感到一种荣幸和自豪。
在办文学社的那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学校好些老师乃至社会上的一些文化名人,其中很有一些热情的支持者,有的竟成了我的朋友。他们都在我搞文学社狂热的那会儿,很是负责任地告诉我: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应抓紧学习。说我考上大学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考不上大学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结果恰恰是我辜负了他们,我没有考上大学。面对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结局,我心里颇感内疚。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去复读,这里面有好多的原因,可是不管怎样,我都感谢他们。我会坦然地面对现实,认真地去努力,哪怕是我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只要我无愧人生就行。
三
在有了“雏莺”的日子里,我总是像牛一样被它牵着鼻子走,一心想要它在自己的手中变成“雄鹰”,这一切似乎对于学生这个称谓来说,不太适宜。我也经常对自己进行反省,然而我很深地陷了进去。所谓的放弃和解脱计划一次次地流产了,另者我的执着倔犟的性格同时决定了我和“雏莺”之间的一切,正因为有了这些,所以“雏莺”决对的不能像同宿舍一位同学说的那样折断翅膀,它要展翅飞翔,越飞越高。
脑海中有了这么一件事,我就得尽最大的能力去办好它。更何况文学梦是我少年时代便怀有的一个梦,“雏莺”是血气方刚的我的第一片天地,或者就像别的同学给我说的“事业”一样。
我有好几个初中时的同学在山西稷山师范学校上学,来信是他们特意给我寄了几份他们学校文学社的报纸。回家时还特意给我详细介绍了他们学校的文学社情况,对于他们学校的文学社情况,我亦早有耳闻。一所普通的中等师范学校便有枣花文学社、太阳雨诗社、黄土地校园文学创作协会三个文学社团,其中枣花文学社的成绩尤其引人注目,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在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遂萌发了去该校参观交流的想法,看看人家文学社是怎样搞起来的,也凑巧正逢2000年元旦学校放假,于是只身一人踏上了去该校的客车。
为了赶时间,那天清晨五点钟便到振兴桥头等车的地方,这比客车的发车时间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冬天的早上五点多钟很黑,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恐怕丝毫也不为过,寒风很是疯狂地肆虐着,一个人踱着步子走在僵硬的柏油路上,脸、手、脚都冻得生疼。身临此情此景,很想打退堂鼓转身回去,钻进温暖的被窝,然而我没有。一想到我们几个的“雏莺”,我便很是坚定地咬紧牙关,结果那次我同该校文学社的几个主要干部交谈了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脑筋中有了好多的新想法和点子。特别是同该校历史最长的枣花文学社社长黄守菊结识以后,通过她介绍他们“枣花”的发展历程,我感到了“雏莺”的希望,更增添了一种信心和力量。回来的时候,我带回了好多的有关他们的资料。也正是那次的交流,回来以后我便将十六开油印的社刊《雏莺》改成后来四开四版的胶印小报。可以说,这是“雏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但那天自己却因忙着交流,一整天都没有顾得上吃一顿饭,只是回来的时候,顺便在途中客车停歇拉人的功夫,买了两个油饼,囫囵吞枣般地咀嚼着。当时一方面是时间紧,另一方面可毫不夸张地说是怕花钱,这次交流所花的钱是我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来的。并不是我吝啬舍不得花钱,如果真舍不得花钱,我便不会来,不来的话一毛钱也不会花的,说到底还是为了我的“雏莺”能够有所发展啊,这件事后来被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研究会会报《学习方法报·文学版》在社团百颗星栏目予以介绍。
说实话,在经营“雏莺”的过程中,我吃了好多的苦,常常为了一期的报纸,为了一次活动,和我的同伴们来回奔波着,我们山区小县印刷条件不好,一期报纸往往得奔波于印刷厂和学校七八个甚至十几个来回。在印刷机旁看着一张张的报纸依次滚动着,也许就是我们热情的象征和代表。刚开始时,文学社连后来的那间卫生间改做的办公室也没有,好多资料和每一期剩余的报纸都在我宿舍压着,很不方便。审稿、开会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只能在别的同学不理解的眼光中呆在教室进行,我们其实也不愿这样,尽管尽量利用星期六的晚上,但教室里还是总有一些刻苦攻读的学生。后来学校拨给我们一间办公室,就是教学楼三楼卫生间改成的办公室,尽管很潮湿,我们却打心眼里高兴,我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再后来。就是我离开学校的那年秋季开学,学校给我们文学社重新调整了一间办公室,很好的那种,我曾去过几次,在布置一新的房子里我想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几个字。是啊,苦心经营的“雏莺”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一般地成长了起来,我又怎能不高兴呢?
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黄土高原上的农家孩儿,家庭境况并不是承包小煤矿和经商的暴发户,是很一般的那种。当我为“雏莺”进行着种种努力,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将许多零花钱贴进去的时候,许多同学便感到不可理喻,说你应该好好学习考大学,办什么狗屁文学社呢?还有的同学脑子比较聪明竟然这样说:“国梁办文学社肯定是有所企图的,要不他怎么回做到那种地步呢?”要说上学时听到这些话时我还感到有一些委屈和不悦的话,那么如今漂泊社会的我,不仅没有了那些感觉,相反还感激那些可爱的同学,别人说你,不管是好是坏,总归是一件好事,证明大家还都关心你。如果大家连你都懒得说了,你也就真的一钱不值了。
的确,我该好好学习上大学的,这也是我所一直盼望的,可是一年年成千上万过独木桥的学生,总有那么一大群过不了桥,虽说国家高校一再扩招。总是看着许多同龄人似乎将整个人生作赌注一般,都押在了“高考”这两个字上时,我自己真的不能理解。特别是看到许多同学明明知道自己考不上的,但还是拼死拼活般将自己定格在那个圈子里,我感到了窒息甚至一种悲哀,虽然考上学校,前面的路就较为之广阔,但是脚下的路千万条,考不上大学就真的死路一条吗?不,不是的。你要发展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正确去认识人生的考验。我没有考上大学,其实并不是搞文学社直接影响的,有好多方面的原因,偏科便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搞文学社,也没有所谓的任何企图,就算有企图,我又能企图什么呢?经营“雏莺”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一种对文学的忠情,打心眼里我真的没有也不想把“雏莺”和利益相牵在一起,以至于我可能因为“雏莺”没有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大家一样进入大学,成为天之骄子,我也没有太多的懊悔。要说懊悔是我对父母的一种愧悔。我没有因为自己考上大学,让他们略感欣慰,相反让他们为我操了太多的心,直到现在还一直为我默默地奉献着,我愧对他们。我的父母是村里很有人缘的朴实农民,是他们对我的一种宽容,让我按照自己的个性一直发展到今天。
四
没有白下的苦,也没有白流的汗,只要你肯下功夫,你总会有所获得的。这是妈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以前的我在经历了一些风雨和挫折之后,再仔细回味咀嚼老妈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我感到了自己的自负和无知,同时很惊讶不识字的老妈竟然能说出这样富有哲理蕴意无穷的话。如同经营“雏莺”的那些日子里,我在辛辛苦苦为其付出的同时,并没有感觉到在这过程中有何收获和进步。但是高考落榜进入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获得,如果没有去创办“雏莺”,为“雏莺”一心一意去付出的话,一旦考不上学校,我真的要卷起铺盖回家和老父一起种地去了。而我没有。之所以没有,一方面是我的性格因素,另一方面恐怕就是“雏莺”给予我的。在经营“雏莺”的日子里,让我懂得了怎样在芸芸众生中去显现自己,怎样去面对困难和挫折。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被社会的世俗淹没,依然在这个物欲横流充满铜臭的社会,寻觅到了一方洁净的天空,任性地挥洒着自己的汗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艰难和奋斗。在这个离家一百多里的小城,一个没有什么显赫背景、家境并不富裕的农家孩儿,如此义无反顾辛辛苦苦追逐着自己的梦,令许许多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感到惊讶,凭的是什么呢?说出这些,大家恐怕就都不难理解了吧!
2000年的五一假期,我放弃了回家一趟的打算,和时任雏莺文学社主编的李彦辉,文学社社员许小雷三个人去了一趟山西临汾《语文报》社和《作文周刊》社。在山西师大主办的全国发行的《语文报》社我们见到了该报副总编辑蔡智敏先生,当我们三个山里娃将文学社社报《雏莺》放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时,他很热情地询问我们的各种情况,谈话中从他的眼里我看到了对我们的一种惊讶。如今雏莺文学社“愿‘雏莺’飞得更高,唱得更美”的题词,便是当时他应邀给我们的题词。那次拜访后的收获,是后来我们社员班筱丽的作品《五月的渡口》在语文报上发表了。
对作文周刊社的拜访,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位姓周的编辑阿姨接过我们的《雏莺》浏览时,忽然说:“赵国梁,谁是赵国梁?”我说:“阿姨,我是,我就是赵国梁啊。”她说:“你是不是写过一篇《甜甜油糕情》的文章啊?”我说:“是啊。”她便微笑着说:“你的文章发表了,报纸已给你寄过去了。”这位阿姨特意再送给我一份登有我文章的报纸,并告诉我《甜》一文获本学年年度奖,将获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优秀小作者夏令营。“真的吗?”要不是有编辑阿姨在场,我准会激动得跳起来。当时心里的那股喜劲,真是不知该怎么形容才好。要知道《作文周刊》是上小学时便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刊物,小时候想着能在这上面发表自己的作文该有多好呢?现在终于发表了,你说能不高兴吗?现在的我作品不间断地发表,却早已没有了那股喜劲。包括前些天在《中学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显得十分的平常,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活得比较现实了。从《作文周刊》社回来以后,我们社员武丽红、史栋琴同学的作品均发表了。其实文学社社员的积极性,就是通过发表作品一步步提高起来的。
那年七月,我在爸爸的支持下真的参加了作文周刊社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优秀小作者夏令营。这可是宣传《雏莺》的一次好机会,出发之前我便将一沓《雏莺》报整齐地放在旅行袋里。夏令营报道的那天,我就不顾将近14个小时火车的颠簸,拿着一沓《雏莺》报穿梭于营员的各个住房之间。我虽然很累,可我不想白白浪费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也是自己的雏莺社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的绝好机会啊,我又怎能将其白白浪费掉呢?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作为四个优秀小作者代表之一到河北三河拜访著名作家浩然先生时,我将《雏莺》报送给了他。还和同舍一位临汾的营员梁胜敲开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神笔马良》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房间门,送给他《雏莺》并请他为“雏莺”题词。现在每每看到挂在“雏莺”办公室墙壁上“神笔马良,和你同在”的几个大字时,我都感到一种骄傲和自豪。尽管那时的想法,如今步入社会的我有时真感可笑,可我为我自己而感到可爱,特别是自己从北京回来一下火车,没有急着去休息,而是在骄阳似火的大中午急着去寻找书画装裱店去装裱洪汛涛先生的那幅题词,很是佩服当时的自己,为自己感动。结果在那次夏令营活动中,很活跃的自己,被委任为夏令营营部领导,还被选为优秀营员代表大会发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学校之后,“雏莺”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函逐渐多了起来。
这些或许是登不上如此大雅之堂的,而我则确实就是在这之中和“雏莺”一样慢慢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记得去语文报编辑部和作文周刊社的时候,李彦辉和徐小雷他们两个都不好意思先敲门,是我撇着一口土气的普通话“勇敢”地带头进去了。也就在这之中,我不再萎萎缩缩,变得能放开自己了,自己放开了,也就懂得了许多,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五
陪伴“雏莺”的日子里,一个人傻傻地趴在桌子上,在稿笺上涂涂抹抹,课余的时间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打发了。一些同学总不明白地认为:你写得再好,文学社办得再红火,你也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你就是狗熊一个,再说那也忒辛苦了,还不如和我们大家一样痛痛快快地玩一场呢。我知道,这些同学是为我好,让我能够上个大学。可有时乃至到现在有些事情我还是弄不明白,人为什么都非得要上大学呢?上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考大学吗?再说对我而言写作和上大学本身就是俩回事,我没有上大学,是好多原因造成的,这些在本文前面我已提到过了。又为何总要牵扯到一起呢?这使我无法搞清楚,无法弄明白。可能本身我就是一个太为倔强太为偏激的人了,但是在考大学这件事情上我不这么认为自己,哪怕说我“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学校时,我曾作为乡宁县学生代表赴省城太原参加了山西省学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宣传“雏莺”又一次使我成为许多代表关注的焦点。印象最深的是晋中灵石一中学生会主席杨芳同学,会议结束后专门和我谈了4个多小时,回去后她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雏莺腾飞,志在国梁》的文章,发表在该校校刊《山花》上。文章的后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和他(国梁)交谈之后,我感觉他特别优秀,也很能干,毅力和任性也很出色……”不怕大家笑话,当学生时我确实这么认为。可已迈进社会一年多的我,早已不这么认为了,自己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人才的,但我还是在烟波浩渺的社会中,踏踏实实地做自己认为该做和喜欢做的事。
随着“雏莺”的成长,我的知名度也慢慢地提高了。2001年元旦学校首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上,有一个《小偷公司》的小品。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你知道小偷公司办公室主任是谁吗?是谁?赵国梁,两个同学为了逗大家乐,专门免费用了一下我的名字,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堂堂学校学生会主席和文学社社长,怎么能成了小偷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呢?笑归笑,笑声中我感到了一种付出后收获的充实。特别是在经营“雏莺”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全国好多个同龄优秀小作者。许多知名的校园文学领袖人物我也认识,像全国中学社团研究会刘解军先生,江苏省邳州市校园文学协会会长吕伦老师,湖北老河口师范《校园文化报》总编辑、《寻路少年》作者秦战勇先生,校园作家《青少年大参考》社主编王改昌、《青青校园》主编柳雁阳、编辑刘大钟、彭绪洛等等我们都有交往。经常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我的许多同学总是很羡慕我的朋友遍天下,每每此时我总是很得意地朝他们笑笑。
六
就像前面所说的,有了“雏莺”的日子,我总自负抑或虚伪地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或许有了这么一种认为,日子总在自己的自我陶醉中过得很快。不管我在高考来临的日子里,感到多么地茫然和困惑。但来的终究要来,“雏莺”和我的故事在我的极不情愿中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去年七月我结束了自己的高中生活,高中阶段我的学业是很一般的,或者说成“差”更为准确和合适。在这种结局下,我没有卷起铺盖卷回家或者咬紧牙关再复读一年,而是早在四月份便在县里的一家金融单位做了一名临时文员,我想之所以有这么一次机会轮到自己的头上,的的确确应该感谢学校校长梁建法老师的大力推荐,说到底也是沾了“雏莺”的光。离开学校,原本不计划参加高考的,然而一想到自己为之奋斗的大学梦,想到自己的前途,便黯然伤神心里像被刀子割了一般疼痛。虽然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定格在“高考”上,但它毕竟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啊,最终参加高考的我,只考了300多分。300多分与儿时上北大的梦想相比,该是一种多么可笑的反差呢?高考结束后,我的心里极不好受,木头人一般,呆呆地向单位走去,眼泪也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走了,“雏莺”还将继续。就在我彻底离开高中校园之后的七月二十五日,我和时任社长的安柯、主编刘瑞菊,以及其他几位社员,赴北京参加了全国中学文学社团研究会三届三次年会。在那次大会上,我认识了一名叫张勒的朋友,她是举办单位北京顺义区杨镇一中的学生,该校毛毛草文学社副社长。有趣的是,在这以前我就读过她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三月三南方·文学网》上的。文章题目、内容均记不清楚了,好像是寒假和爸爸到北京商场购物摸彩票的事吧,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这并无关紧要,关键是我们很谈得来,真可谓正宗的以文章相会的朋友。回来以后,我们通过几次信,她帮了我许多忙,还特意给我写了一篇《朋友,我们都是十八岁》的文章。然而我却因为太忙,给她买一份礼物的想法也总一次次地被搁浅,以后有机会再补偿吧。
在那为期五天的会议里,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再享受到了“雏莺”带给我的荣耀。作为该会唯一的一名高中生理事,参加了理事会。我们的“雏莺”在我看来理所当然地囊括了所有的奖项。直惹得广东连州中学燕喜圆文学社的李振刚同学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好风光啊。”当我和安柯捧着“全国优秀校园文学社团百面旗”和“全国优秀样板社刊(报)”的两枚铜牌时,虽只一刹那的时间,我却想得很远,但也异常地平静,根本没有像原来想像的那样哭出声来。
过后自己想,要是和我一起创办雏莺文学社的李彦辉在场的话,我们可能都会哭出声来,他是我在经营“雏莺”的岁月里,最好的一位搭裆。有好多原因,他未能和我们一起领奖,我的心里颇感失落和愧疚。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班的,因为“雏莺”我们走到了一起,亲如兄弟。他对我并不像其他朋友和同学那样,一味地对我大加赞赏,总是很直接的指出我的缺点和不足。虽然他考上了大学,前途可能比我要强得多,但“雏莺”岁月,会使我们永远情同手足。
七
到这儿,似乎再说别的话,便是多余和累赘的了。可惜不是,去年十一月,学校联系县电视台给“雏莺”拍了一部专题片——《希望从这里放飞》。其中有对我一个短短的介绍,坐在隔壁那间图像不清的电视机前,看到那段时,我是感慨万千的,要不是好多人在场的话,我肯定会掉眼泪的。
离开“雏莺”的这些日子,我四处艰辛地奔波为自己的另一种选择,我无悔“雏莺”岁月,虽然没有考上大学是我心里最疼的一个伤疤。
感谢“雏莺”岁月中,给我帮助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以及其他可爱的人。祝福和我一切为“雏莺”腾飞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同伴们。
别了,“雏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