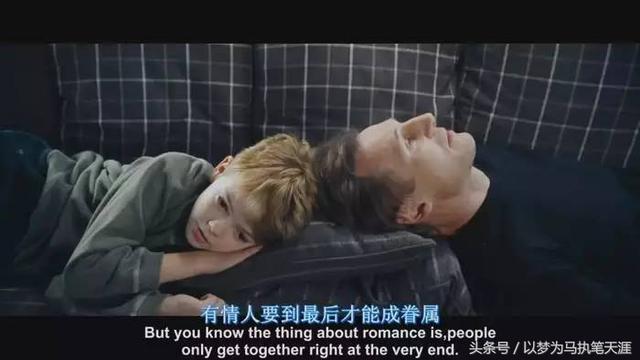星期一的时候,她没来,第一排留下很显眼的空位。问同村的孩子,都说不知道。打电话到家里,长长的响音之后是无穷尽的忙音。我的心一下被扯得很远,该不会出什么事?因为,她是一个从不迟到的学生。
中午,我决定去她家看看。这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孩子,高而美丽,脸上点缀着永远的腼腆、永远的笑。在新年联欢会上她还唱了一首《栀子花开》,同学们都说好听。
家里没人。邻居说她走了两天,大概是去看病。
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复习中。临近年关,外出打工的父母马上回来,谁不想多考两分抚慰一下疲惫的父母。我忙活着,出卷,批阅,分析,不敢有一丝马虎。
至于她,我们暂时忘记了。不久,便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校长告诉我,李娜在蚌埠治病,打电话让我向你请假。什么病?校长摇着头说,“不知道,她父亲急急的,说完就挂了”。接着,就有和她同村的老师说,确诊了,是白血病。白血病!我瞪着他,企图挤榨出一些谎言。20天前还清纯地唱着《栀子花开》;4天前还履行着团支书的职责,腼腆地走上讲台安排工作;刚才还读过她写的一篇作文……然而那老师摇摇头,“我也不希望是真的”。
我更不希望这是真的。短暂的几年教学生活,我习惯了看着一个个流鼻涕的儿童变成含羞的少女、阳光的男孩,习惯了与这些纯真、快乐的孩子相处的感觉。我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绝望,好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摧残过的断枝残花的绝望。
于是,我回到家,查资料,翻开所有的书查。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精神慰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星期三平静,没有好消息,但也没有坏消息。我开始乐观了,也许是讹传,或者是误诊,信息时代古老的错误依然存在。校长说,明天我们一起看看,表示一下心意。记起班里焦急的孩子,我想带两个去。校长考虑了一会儿,就说,算了吧,路远,学生正复习。我想也是,找出联欢会的录音带播放,里面有她的歌声,让同学们听了,抵消了一些思念。
那歌声像花香,轻轻地弥散。
愿望与客观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星期四,一切都回归残酷的真实。在离家十公里的一个医院,李娜已经失明,已经昏迷,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一切来的那么突然,总让人认为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玩笑或是生活的一幕戏,这是未曾料到的。
我和一个同事匆匆坐上车,车里竟有街上许多熟识的面孔。我们相互点头示意,我们有同一个目的,去探望女孩,还有寻找希望、奇迹。
病房外面站着李娜的父亲,那个瘦瘦的公务员。人群中,有人突然抱住我,痛哭起来,机械的、语无伦次地絮叨,我无法劝说。直到有人把他拉开,我干涩地说,我想看看孩子,这才走进病房。那个叫李娜的孩子,我看到了,安静地躺在床上,脚快伸到床头。几根白色的管子,蓝色的氧气瓶,还有她的鼻孔,她的身体,它们此时是一个整体,床边围满了人,坐着,站着,蹲着,都在抹眼泪。一个妇女一边哭一边诉说着什么。终于,一个长辈训斥着,不要哭,她能听到,然后开始向外赶人。但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乡邻、亲戚、熟识的人都赶来看望临终的李娜,看望曾经美丽、腼腆的李娜。哭,似乎成了唯一的语言。
我的到来让她母亲又找到了新话题,她拍拍孩子的脸,摸着孩子发青的胳膊,告诉李娜:“老师来了,班主任来了,你不是要考试吗?班主任告诉你不用考了,课,他会帮你补。”我蹲下去,看看李娜那白的脸,长的睫毛,准备好的话,譬如深情的呼唤、旁若无人的鼓励都搁浅在嘴中。她睡熟了,静谧,安详。突然,她急促地呼吸起来,脚猛地动了一下。那个长辈告诉我,她看不到,还能听到。你来了,她高兴。分明地,她眼角渗出一滴泪水,向下,向下,在她昏迷的世界里,老师竟然还是一丝光亮。她酸楚哽咽,无法控制。医生快速地跑过来。我后悔我的到来让她激动,但我奢望她的激动能带来奇迹。我只好默默地祈祷,默默地看着人来人往。几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我该走了,让后面的人表达心情。门外,遇到那位长辈,我悄悄掏出一百元钱。他并不拒绝,我有了一丝安慰。这种纸质的物品,写上数字的物品,能够传递一种心情,我已经很满足了。
走出院门,我忍不住又回去看了一眼。她还是平静地睡着,床头堆满了亲戚送来的新衣服,还有一个胖娃娃,开心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