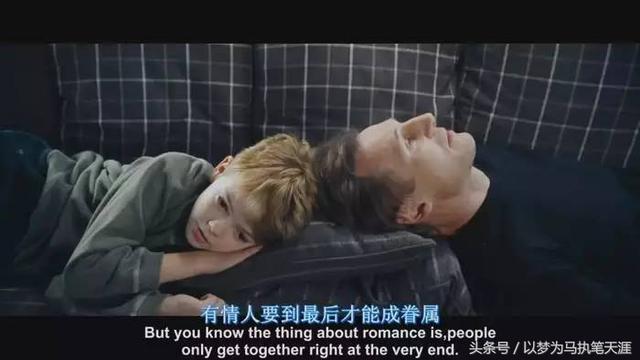我的初中是在县里的一所民办学校读的,当时,在我们那里,它算是条件最好的民办学校了。而且,据学校说,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与那个县里升学率最高的学校完全不同的:那学校只是应试教育,而我们学校则是素质教育;他们的学生进入高中后会全面倒退,而我们的学生则会全面发展;他们的学生考试是作弊,而我们学校的都是实力。类似这样的很多东西,这都是我们的老师所对我们讲的,我们只记在心里。
在那里,我除了刚到的前半个学期有点困难外,其它的都还可以。毕竟,分数才是硬道理。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成绩好,你想走老师都要拉着你,但是,成绩差的,老师可是巴不得你马上就走掉的。
那时,我们班主任是那年我们学校创下了一个奇迹——将一群所谓的乌龟变成了超级兔子的教师。两年前,我的班主任接手了一个由其他班甩出来的学校都不想再管的学生,经过她两年的“教化”,也便创造了那个奇迹,他们乌龟班的升学率居然超过了兔子班。我的班主任是我们语文老师,据她说,那年她所教班级的语文人均分是全县最高的。
起初我是在三十班,而她带的是二十八班。入学考试之后,也便被分到了二十八班。
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只是基础比那里的人要好得多了。我小学的时候根本不怎么读书的,所以我刚开始去那里便是以一种小学态度的延续去读书。如果是在其他班的话,那完全是被允许的,但是,那是二十八班,她所管理的班级。所以我是吃了很大的亏的,耳朵被扭过,手板被打过,马步站过,背不下书的时候,自然也被饿过。所幸的是,没有多久便期中考试了,那次我成绩不错,所以她比之前看得起了我一些。但我不读书的那种习惯始终没有改,到改的时候已是初一下期了。
那次是她预测我又要考全班第一,结果我考了第七。打那之后她再也没有预测过。而我,也因此而变得在乎起那些所谓的没有用的名次来。那年的最后一次考试,似乎我真的有如她以前所说的,我潜力最大。那年我第一,全校。
说真的,对于我来说那真的太意外了,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能够做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也只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并没有什么压力什么的,只是我不再像之前那样地不努力了,因为之前我很讨厌英语的,从那次之后,我甚至喜欢上了英语。所以,我又迎来了第二次的第一。那时,我觉得有了些许压力了,努力了些,而我的目标明确到了极点,那便是卫冕!果然,我又成功卫冕。而到了那时,便觉得有些索然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来了一个与我相当的人,而且那年第一次考试即将我杀落马下。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爽的,想起当日自己走入教室旁边的那些人对新同学说:“瞧,就是那个男生,连续三次全校第一。”觉得很是没有面子,所以我努力得多了。你知道一个智商不算低的人当他真的用心去做一件事时有多么可怕吗?末考前的一个星期,我每天的睡眠都在四个小时左右,想起来都怪可怕的,而且白天的精力也是特好。那即使是如今每天无所事事的我也是做不到的。
那是二十八班光辉的一页,也是我光辉的一页。那次,我以绝对优势领先。我们班也以绝对的优势领先,完全打破了入学第一个学期的那种似乎低人一等的窘迫。而他,却跌落到了第五去了。也就是那年,我们的初二宣布了结束。
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这已是大家都知道了的。由于语文里面的作文这一块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她一直以来就强制性地让我们背记那些参考书上的课外知识。而每次考试都有诗歌默写,所以,每个学期下来,我们本期学过的诗歌默写的次数都在五次以上。再加上她对卫生要求很高,使得卫生委员对我们甚是苛刻,我们都好讨厌卫生委员。那个卫生委员长得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丑,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外表还是她那过于死板的作风,让我们甚是反感。更无语的是,她还要我们作死地背书,背不得的先留着,等背了再去吃饭。更无语的是,她居然还要求我们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下午进教室学习。那些年,大抵我吃饭的速度是很快的,要不还不得给她批死。
初二之后,我们也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初三。
那年暑假我们玩得很疯,很疯。每个下午都不吃饭,或是吃冷饭。每次下课铃声一响便跑了,跑到外面去占场子。我记得,那时正好流行打篮球。每个下午,斜阳,余晖,暖暖,我们八人一组占着各自的场子。我记得那年我将我的兄弟叫去了,去补课的,不过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本来留他到那里读书的,由于他家人的原因也便没有留成。
正式开学后,我们便几乎戒了篮球,投入到备考之中了。那时,我们的课业很是忙的,因为要用半年完成一年课程的教学。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只是要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时我记得我们平时所用的时间大多就是在语文的背诵上。天天背,也不知道在背着些什么,反正,班主任说背哪里,我们便去背。
那时,本来我们学校在星期天的下午还是放假的,但是,那是学校而已,我们直接受管于班主任。那是很黑暗的时光了,我们每个星期只有星期天的两个半小时足够我们去做点事。本来大家都可以轻松下了的,而我们却依旧坐在教室里。我们的教室夹在中间,所以,那个时候,很是无语,这边是电视的声音,那边还是电视的声音,即使将门窗全部关掉,那种声音依旧盘旋在耳边,只是稍微小了一点点而已。那时,两头再美的音乐对我们来说也只是的一种折磨而已。
如果说平时只是帮我们把那些琐碎的事情集中起来,那星期天算什么呢?难道也是将那些琐碎的时间给集中起来?相反,我们倒觉得那只是一种对于我们自由的剥夺而已。于是,我们都很讨厌我们的班主任,因为她连我们一个星期里那最后的休息时间也给剥夺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初三的第一学期,我们还把之前的那种优势给延续了,那年,全校前十我们班七个。
到了第二学期,除英语外,我们的课程几乎上完了。那时,还是作死地背书,语文,语文,语文。似乎我们班就是为了语文而存在着。
我不再背书,因为我对它们已经都很熟了,自信地认为已经足够应付考试了。本来以为只是我一个人不背书的,可是,慢慢地,我发现,不背书的,其实不只有我,其他人基本上都不背书了,尤其是语文。不过,也是那年我开始背记大量的课外知识,诗词抑或是俗语。可惜的是,那里的条件并不好,尤其是在图书上面。我记得我们那里好像不曾有过图书馆这个概念,要不我非得看大量的书不可。不过,我们那里也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小说,只是我一直都对小说抱有偏见,所以未曾看。那年他们看的是言情小说,班主任发现后,痛心疾首,她说:“你们体育老师说这样的书他都不敢看。”那年我们的体育老师才毕业没多久,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用帅来形容的一个小伙儿。那次,惩戒很严厉,那些看过的都让老师叫到了办公室去了,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甚至有不少人还哭了。至于有没有漏网之鱼,我不得而知。
而那年,我们那里也开始流行一种叫电子词典的东西。其实,那东西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在我们那里也不多,之前我们流行的是复读机,而复读机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还不如一部结构简单的录音机,至少那更方便。那部学习机是文曲星的,才一百多而已,但是上面的游戏确是很多。我也玩过,感觉还不错,所以,那年我也买了,只不过,我用的是步步高4988,应该是这个型号了,已记不太不清了,因为它对我的意义远不及我之后所用的快易典V650那么深远,那个段往事,我永远不会忘的,只是,这是以后可能提及的事了,所以在这里不便做过多的阐述。
那时,我不能说班上已没有了努力的人,但是,那些强手,也就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大多是没有努力的,上课要不是玩游戏,要不就是写写东西。我记得,我写随笔之类东西的习惯就是那年养成的。人无聊的时候总会做点什么的,而我,则把我的精力花在了那些与学习无关紧要的文字上,不可谓不“大逆不道”了。
那时,我们还在学校的寝室里面喝啤酒。我是寝室长,而那时我们已不再像之前一样都是好孩子了。只是我不怎么喜欢那东西,所以,每次都只是表示个意思,有个时候沾都不想沾。不过,那些人硬是要我沾上,因为只有我自己沾上了,他们才有安全保障。
之前的我,很听话,有什么不对,都会直接告诉班主任的。现在想来,真的有着几分打小报告的感觉。到了那时,谁管那些呢?我们都想初中生涯早点结束,然后进入那传说中很是自由的高中。这是真的,最想得到的,我们认为最珍贵的,总是那些不曾拥有的,那时,我们向往高中,那片充满自由的乐土。
我的成绩自然是没得说的,但是那年平时的我状态很是很低迷。她便经常问我怎么了,我只说“我怕考不上。”那是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借口了。她只对我说“如果你都考不上了,那这个学校还有谁考得上?”那时,我不知道我是否感动了,反正我是说了“谢谢”的。
对于她我本来是畏惧的,到后面自己在那里有了点成绩之后,那畏惧便转变成了敬畏,再到之后厌倦了那种似乎永无终日的背课本生活,也便在敬畏中再添加了一种厌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对她始终是有着畏惧成分的,也许只因为她是我的老师,而且一直都对我很好吧。如果说老师对学生好是应该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是你?毕竟有着那么多的学生,而且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她所欣赏的学生。在那里我的智商也不是最高的,最多是第二的。在他来之前,我可以藐视任何一个人,他来了之后也便内敛了许多。只是,那年他没有考出一份让自己所满意的成绩,更没有考出一份让她满意的成绩。
考试前几天,她居然对他说,如果你没考全县前五的话,那是很悲哀的事了。而考试的结果是让人很痛心的,他连两百都没有入围。那年我在全县都已经排在一百多名去了。其实,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早在之前,他说,他摸底考试的成绩在以前的那个学校,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另一所学校排名都是在一百名去了。其实,他以前就是那个学校的,因为依靠智力上的优势,过于叛逆,学校也便不再收他。也许是真的吧,他在那里并不显得重要,学校们要到不是智力,而是成绩,毕竟他的成绩在那里也只是中等而已,走了对于班上的发展还更好。但,在我们学校就不同了,我们学校多是一些底子很差的学生,像我这样的学生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有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去那里读书了,我能够坐在这里写东西吗?也许不会了吧。我是需要自由发展的那类学生,自由的心如果被束缚了,那将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了,只是,那些适当的束缚对于我这类介于天才与常人之间的人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很多人都很聪明,但是,有几个能够被称之为成功者的?如果没有束缚,那就只有与成功无缘了。而那时,那所学校与我们当地的一中是一个等级的,当然,那只是从升学率来讲的,而我们学校与二中也不是一个等级的,至于三中,我们学校里面的教师也一直都说和我们是一个等级的,当年我们信以为真,但是是不是一个等级的现在已是很明了的事了。而且,在这里,我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民办学校呢。所以,当年我能够入围两百之列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
那年我们什么都不懂,只是很反感班主任的做法而已。
在升学考试的那段时间,她做我们学校的领队(那年考试改革,我们要到外校考试),还是那么地苛刻,似乎她永远地都是那样的。
我记得她曾对我们说过,她的心脏有病。可是,她为什么还要那样对我们呢,那不是在气她自己吗?
考完的那天晚上,她哭了,真的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因为,她借的一副眼镜学生用过之后却没有还回去了。那是借了她所教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弟或是学妹的,她说:“你们太让我失望了。”那晚,我们都很愤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她否定了我们全部,还是因为那个不敢承认是自己拿着那副眼镜的人?我们不知道,都不知道。那晚,我们通宵,没有回寝室睡。很是无聊,我没有哭,好像也没有人哭。因为,那会不值吧,她对我们太苛刻了,为什么为她哭呢?至于同学之间,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爱,只知道有种感觉很温暖。那年我的同学,有深,有卓,还有建。那年,我们都没有哭。她哭了,哭过之后,又和那些人打起了麻将,笑声充斥着整间教室。她真虚伪!
我们是被锁在了教学楼里面,那次,据说是我们学校第一次毕业生集体通宵。教室里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往日的滋味,只是灯光似乎比往日的要亮了许多。所以,等到午夜之后又不少人都睡着了,就趴在桌子上,像我们平时午睡那样,亲吻自己的手臂。
那晚的钥匙是她拿着,唉,为什么最后一夜还要把我们关起来?
第二天,我整理好东西再找她结算完自己的生活费后,只淡淡地说“谢谢您这三年以来的照顾。”那时我的眼睛大抵是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不多玩几天吗?”
“嗯,不了。”
“哦,那你以后好好加油,一定要相信自己,如果我都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做不到。”
“嗯,我会的。”
“以后有空就常来玩。”
“嗯。”
“路上小心。”
“嗯,谢谢您这三年来的照顾。”我再强调了一遍。
……
我走了,除了那寥寥的几句生硬的话语话以及那三年来的故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在那时,我已将自己的灵魂的一部分连同自己的目光一起埋在了那方不大的地板上。
那年,我没有看到看到那荧幕上常见的泪水,没有相拥而泣,也没有老泪纵横,没有挽留,也没有送别。
“原来你还是那么地苛刻。”隔着车窗我对自己说。
那之后她没有再在那个学校做班主任,那年我们班的成绩也没有学校所预期的那么满意。她说,她不想再做班主任了,因为她的心脏有病。我只无语。现在,她还是在做班主任,只不过是陪着一群孩子,工资不多,却也快乐。
现在想来,那年的我,似乎早已有了如今段氏的高傲,并且高傲地堕落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似乎,那年他们都感染了我段氏的堕落。没有段氏的资本,却也堕落了那么一回。呵呵,那段青春,涩涩的,也许,那晚,我们都被她感染了吧,只是我们太高傲,太堕落,堕落得忘了究竟该怎么哭。笑,也便笑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记下了那些堕落的时光,铭记了那段刻骨的苛刻,那个人,我们也将一直敬畏着。
如今,时间的那段渐远的背影告诉着我,那年、我们都很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