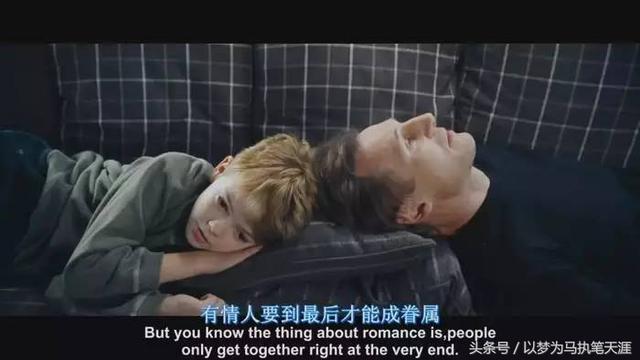她理想的男子是高大,瘦削,有一点黑,斯文,有一双忧郁深邃的眼睛。她在纸上画,画到最后,才发现仍然是Y的样子,她高中的老师。早就死了,是她高三的时候就患癌死了。她画的永远是Y上课时的样子。斜靠在一张课椅上,手里拿着半截白粉笔,搓着沾在手指上的白粉,眼睛望向窗外,沉浸在自己所讲的内容中,有些出神和忘我。
她才13岁,早熟聪慧的女子,但是很捣蛋,像一只还没长大的小兽。住校生,总是不做作业,上课讲话,坐得东倒西歪,跟男生打架,早上起不来,晚上睡得早,但功课很好。她在周记本上写:哎,完了,这个学期的化学习题几乎没做,要考砸了。他用红红的笔批注:“不做怎么可能有收获!”打了一个红红的感叹号!她不知从哪里抄了一段生肖的命理,后面加了些小儿女的对照慨叹,权充每周的交差。他又用红红的笔写了很长一段,不要相信命运,列举她好几处优点,勉慰她一阵。她看的时候真是感动,但顽劣心总是不改。他时不时地把淘气的她单独拎到办公室面谈,和善地,却话很少。一排平房前,一个花圃,院落里有一株巨大的雪松,下面开满栀子花,高大的他耐心弯下腰,让她坐在一张藤椅上,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不多的话题:不能不做作业,要努力,要认真。她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他那双深深的眼睛,而他的眼睛也总是往别处斜看着一点。
高二的时候分班,她听了Y的话,选了文科。Y是学历史教历史的。他把她郑重托付给新的班主任。她仍然顽劣难改,成绩永远很好,但永远做不了第一。只是她的历史成绩突然平庸,全无灵性了。Y因为教学理念与校长发生冲突,正试图调离学校。很少能在校园里看到他,即使见到也是匆匆一笑,先生好,打个招呼停顿一下。
噩耗传来,她永远不记得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怎么回忆都是空白,高三的冬天,一群周日仍在早读的同学,不知怎么外面躁动起来。大群同学拥着去看,Y的妻子到学校来处理后事,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很高大,面目清秀,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有点臃肿,神色悲哀。
她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么多。只有这么多。她写信给师母,字里行间地安慰了她,也回忆了Y对她们的关照。她给她寄了一张他们的结婚照。5寸的老式结婚照,假的背景,旋转的楼梯突然断了头隐没到更假的空间里,Y跟穿白色婚纱的新娘长身玉立地站着,脸上微微浮起笑意。从那以后,她突然不顽劣了。她变得沉默又高傲,吃完晚饭后,跟不多的一两个朋友散步到学校外面的村庄,爬到一个废弃的砖瓦厂的高处,远远地看着夕阳惨烈地下坠,世界一片通红。一片安静,吹着风,到处都是荒草。什么都没有。
好多年后,她有时还会想起五月的光景,开满白色栀子花的小院落,有一株大雪松,夜色静谧柔和,那里伫着一个少女的心。还没盈满,就被咬掉了一块。她永远是缺了一块的。